|
带着盛夏的气息,北京进入了持续高温天气。在老舍笔下,北平的夏天西瓜甜,香瓜香;梁实秋眼中,夏天最惬意的事是来一碗沁人心脾的酸梅汤;朱自清徜徉在荷塘月色里,流连忘返;汪曾祺则爱在夏天里看花儿,他认为最幽静的是珠兰……夏天在名家的笔下充满趣味,也弥漫着诗意。快来读一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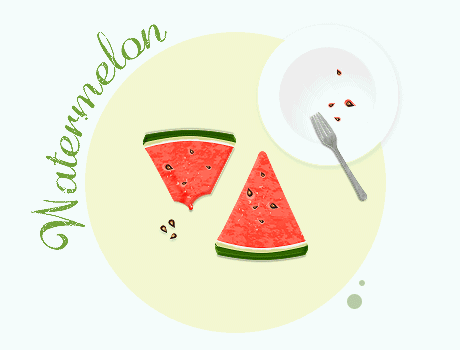
闲:西瓜甜,香瓜香
老舍:《北平的夏天》
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仕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金黄瓤子的“三白”与“哈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而“老头儿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向隅的。

梦:光影梦幻
朱自清:《荷塘月色》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花:珠兰最幽静
汪曾祺:《夏天》
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珠兰。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秋葵也命薄。瓣淡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凤仙花有单瓣者,有重瓣者。重瓣者如小牡丹,凤仙花茎粗肥,湖南人用以腌“臭咸菜”,此吾乡所未有。马齿苋、狗尾巴草、益母草,都长得非常旺盛。淡竹叶开浅蓝色小花,如小蝴蝶,很好看。叶片微似竹叶而较柔软。

沁:来一碗酸梅汤
梁实秋:《酸梅汤与糖葫芦》
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地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避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件“冰碗”,莲蓬桃仁杏仁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地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冰泌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酽,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们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尽七碗方始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谗。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成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一“可口可乐”到处猖狂。

趣:男孩们的童年往事大多在夏天
冯骥才:《苦夏》
男孩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书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

静:凝神沉思,鸟雀在唱歌
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
第一年夏天,我没有读书;我种豆。不,我比干这个还好。有时候,我不能把眼前的美好的时间牺牲在任何工作中,无论是脑的或手的工作。我爱给我的生命留有更多余地。有时候,在一个夏天的早晨里,照常洗过澡之后,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或默不作声地疾飞而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或者远处公路上传来一些旅行者的车辆的辚辚声,提醒我时间的流逝。我在这样的季节中生长,好像玉米生长在夜间一样,这比任何手上的劳动好得不知多少了。这样做不是从我的生命中减去了时间,而是在我通常的时间里增添了许多,还超产了许多。

海:夏日的气息
村上春树:《且听风吟》
好久没有感觉出夏日的气息了。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肌体的感触,洗发香波的气味,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然而,这一切宛若移动过的复写纸,无不同原有位置有着少许然而却是无可挽回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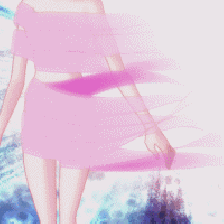
风:云在风中走路
顾城:《窗外的夏天》
我们年轻 什么也不知道 不想知道 / 只知道 梦会飘 会把我们带进白天 / 云会在风中走路 / 湖水会把光亮聚成闪烁的镜子 / 我们看着青青的叶片 / 我还是不想知道 / 没有去擦玻璃/ 墨绿色的夏天波浪起伏桨在敲击 / 鱼在分开光滑的水流 / 红游泳衣的笑声在不断隐没 / 一切多么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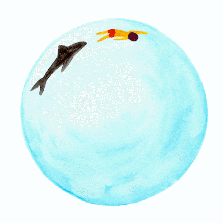
耍:西瓜皮是我最好的泳帽
苏童:《夏天的一条街道》
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是为了不失时机地早早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黄昏时分驶过河面的各类船只小心谨慎,因为在这种时候整个城市的码头、房顶、窗户和门洞里,都有可能有个男孩大叫一声,纵身跳进河水中。他们甚至要小心河面上漂浮的那些西瓜皮,因为有的西瓜皮是在河中游泳的孩子的泳帽,那些讨厌的孩子,他们头顶着半个西瓜皮,去抓来往船只的锚链。他们玩水还很爱惜力气,他们要求船家把他们带到河的上游或者下游去。于是站在石埠上洗涮的母亲看到了他们最担心的情景:他们的孩子手抓船锚,跟着驳船在河面上乘风破浪,一会儿就看不见了,母亲们喊破了嗓子,又有什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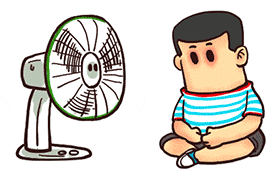
热:热到站在泳池里听报告
池莉:《武汉的夏天》
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得传神。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于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我答:摄氏42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于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于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作报告。武汉三镇,数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到了作报告的时候,于光远先生一看,是在东湖的游泳池里。于光远先生坐在游泳池边沿讲话,听报告的人黑压压一片,都站在游泳池里。听的人倒不错,唯独热坏了于光远先生一个人。于光远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八十多岁,所经历的最热也就是武汉的这一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