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被革命洪流卷进大时代海洋里”的人们——《金光大道》文学赏析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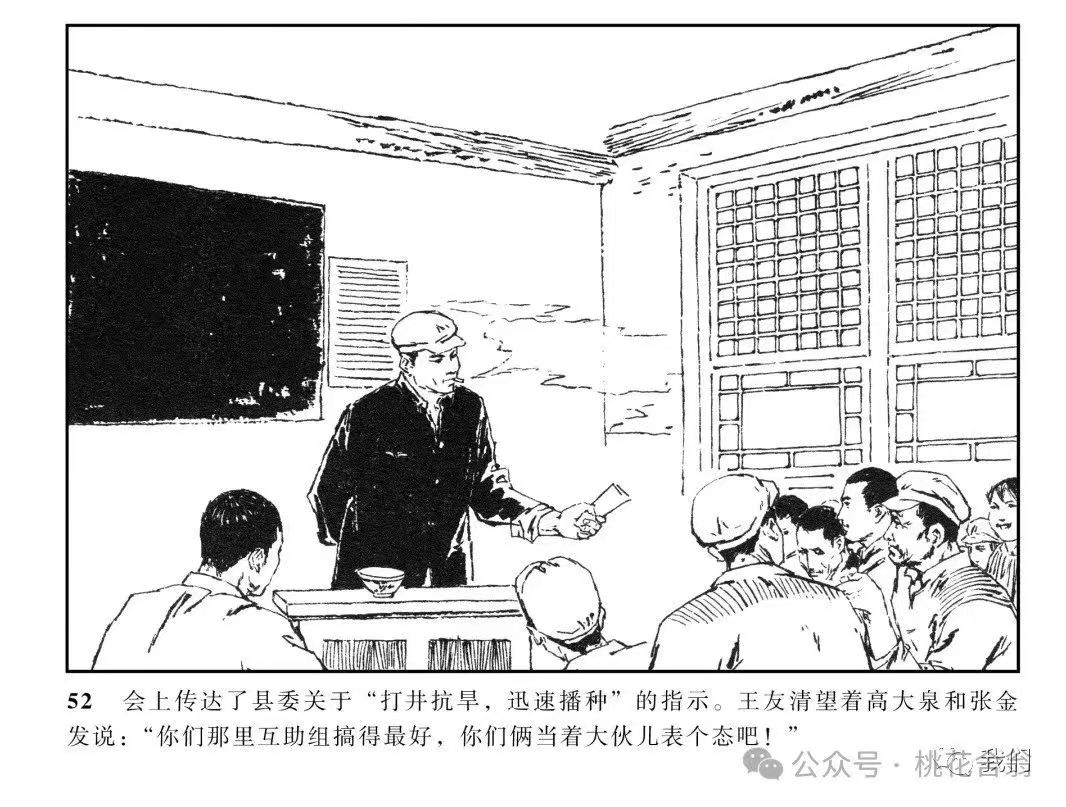
《金光大道》描写的众多人物中,区委书记王友清着墨不算多,但仍令人印象深刻。
王友清出身于下中农家庭(“是一个界于贫农和中农中间的那一类庄稼户”),因为在同本村一户“霸占了他家仅有的一片枣林”的地主打官司时得到根据地抗日政府的坚定支持,“轻易地把官司打赢了”,“感激恩德的思想促使他靠近了革命,积极地参加了村子里的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那个地主的小儿子“随着国民党的队伍开过来”,声言要找他“报仇雪恨”,他“被迫离开了农家院,扛起了枪杆子,为了消灭仇敌,为了保护自己”而战。所以,王友清成为革命者带有较大“感恩”和“被迫”的因素,而不是出于思想觉悟。
小说中一些故事,生动刻画了他这类“革命者”:
全国解放后,“穿着干部服装的农民”王友清因迷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太平日子,曾“像迷了心窍一样,三番五次要求退职,甚至宁可受党纪处分也要回家当农民”。“当时还是副县长的谷新民狠狠地批评了”他这种“狭隘的农民意识”,并让他到地委党校学习。他“服从了组织”,但是“并没有心服”,一度成为有名的“退坡干部”,直到后来“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提拔为天门区的区委书记”,“他看到自己的前途”,才变得“工作很积极,学习很努力”,“连生活作风、一举一动都起了变化”。
因为受过谷新民的“亲手培养和提拔”,王友清“尊敬这位老首长,对他有言必从,有行必效”。土地改革结束后,谷新民大力推行农村“发家竞赛”政策,王友清也就积极地传达。当高大泉对此有疑问并提出为什么不赶快搞社会主义时候,王友清“十分果断地告诉他: 社会主义要搞,什么时候搞,那是上级的事情,下级只管执行就对了”。可见,“有言必从,有行必效”是他自己对上级、也是他希望下级对自己的“行为准则”。
第一部四十五章中,看到高大泉和朱铁汉向上级党组织写来的反映芳草地村在“发家竞赛”的影响下“春耕实际上搞得很糟”、“我们很担心分到的土地保不住,农民支援不了工业、支援不了志愿军”的意见信时,王友清的表现很生动:他先是立刻“就火了”,“腾地站起身,冲到屋门口”,但随即“又把迈出门坎儿的一只脚收回”,并“不由自主地捏了捏衣兜里那个”把芳草地村列为“发家竞赛促进春耕生产的典型”的接受记者采访“谈话提纲”,然后“慌乱地转了个圈子,重新坐在椅子上,把那信又看一遍,心里增添一股说不出来的烦乱感觉”,暗斥高大泉他们是“胡说八道”、“故意捣乱”、“岂有此理”,而“当他怒冲冲地把这封短信看了第三遍的时候,忽然冷笑起来”,此后在向县长谷新民表达看法时,就以“平静”的态度、用“这信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充足理由”否定了这封信。这一段的一系列动作描写,使王友清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变化呼之欲出。
第二部三十五章,高大泉发现县长谷新民引进的“生产自救”项目(外地资本家到天门镇开设“临时鞋场”,由乡村农家妇女帮它加工鞋底子以换取小米报酬)中,资本家用掺夹马粪纸(黄色草纸)的鞋底制作志愿军的军鞋,立刻向区长田雨汇报,恰好这时鞋场的权经理为了掩盖罪行,带着“两袋白面,一扇猪肉,十几瓶白酒,还有五六条香烟”找到区委书记王友清行贿。田雨让人把王友清请来商量:
“王友清满面红光地走过来了,一手摇着黑色的折扇,一手夹着多半截的香烟,他那眼神和情态,掩饰不住工作上十分如意的心气。……秋后一算帐,今天的红火,那时的成就,天门区就要成为模范区,他就是这个模范区的区委书记……
他笑容满面地对田雨说:‘老田呐,本来有个急事情想找你商量决定。……’
田雨说:‘芳草地的高大泉回来了。’……‘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新问题,得马上处理,咱俩先交换交换看法。’
王友清说:‘我也等着跟你交换看法,决定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鞋场的工作开展得挺不错,厂方对咱们也就挺满意。刚才权经理带着两个伙计送来一点东西,表示对区里同志的酬谢......’
田雨反问:‘你打算接受他的这种酬谢吗?’
王友清说:‘所以我要跟你商量商量。’
‘你的意见呢?’
‘我一再推辞,他非留下不可,硬是拒绝,又怕影响关系。反正只是一点吃的东西,放在厨房,让大家改善改善,也没啥了不起。’
‘不,依我看,那不是一点吃的东西,那是毒!’
‘什么?毒?’
‘这些钱串子,绝不会无故贿赂我们这种人!’
‘老田呐,瞧你,又不是金银财宝,哪能用贿赂这个词呢?当然,对处理这点礼物,如果咱们的意见不能一致,我也不坚持,可以请示谷县长来决定。’
‘不是请示谷县长,是向谷县长揭发、控告,这些资本家罪恶滔天呐!’
王友清被他说得莫名其妙,瞧见他气色严肃,只好先不争论, 听他说下去。
田雨抑制着激动,压着声音,把高大泉揭发的问题从头至尾地向王友清述说一遍。王友清听着,似信非信地低语着:‘每个中国人,谁没有尝过战争的味道?人家志愿军在枪林弹雨、冰天雪地里拚命,保卫和平,也保着他们资本家的生命和财产,他们哪能那么没良心呢?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田雨说:‘这就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不是什么良心不良心的问题。事实俱在,我们都得承认呐!’
王友清甩掉了烟头,说:‘你先别急忙下结论,是真是假,等我亲自调查调查。’
高大泉……奔过来,把那只鞋底子举到王友清面前,说:‘王书记,您看看,这不是真凭实据吗?’他用手撅着鞋底子,让茬口上的纸露出来……
王友清从高大泉手里接过鞋底子,看一眼,心一沉,又看一眼,心一跳,胸口扑通扑通地打起鼓来。他在原地兜了个圈子,用扇子骨拍打着大腿,结结巴巴地说:‘真、真没想到,这些人,这样的狼心狗肺,决不能饶了他们!’他说着,气哼哼地转身往回走。
田雨见此光景,眼晴一亮:从这位区委书记的身上冒出这样的火星,多么让他高兴呀!他本来想拦住王友清,研究一下斗争的具体办法再行动,转念一想,王友清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举动很不容易,应当顺势扶持,即使这样冲上去莽撞一些,却可以借机燃烧起来,免得因为习惯的冷静使火星熄灭。……他一边走,还一边给王友清鼓劲说:‘老王,你这样做最正确,我完全拥护。我们遇上了这样的事情,必须坚决斗争,不然,知情不报,可要犯大错误!’
这句话完全说到了王友清的心坎上。他能够掂出这件事情的份量,这种份量,是激起他怒与火的主要动力。他不能跟着资本家蹚浑水,一定得洗刷得干干净净,就算这个临时鞋场因此关了门,他也不能包庇他们!
……王友清怒气冲冲地转了回来。权经理赶紧欠屁股、点头、让坐,机灵的家伙立刻从王友清的脸色上感到有点不妙,忙说:‘王书记公事繁忙,我就告辞了……’
王友清把手里的鞋底子朝权经理眼前一举,说:‘你别走!说一说这鞋底子是怎么回事儿!’
权经理吓了一跳:‘王书记您怎么啦?’
‘你说说,这里边为什么夹着纸!’
‘这,这,这不是敝场的产品......’
跟在后边的高大泉冲到权经理跟前说:‘你敢耍赖?……’
……田雨趁这个空儿跟王友清交换一下意见,问他这件事情怎么收场。王友清一则心慌意乱,拿不出主意,二则也怕弄不好,负责任,就说:‘事情来得突然,时间又紧,来不及仔细商量了,你就先按照自己的打算安顿一下,咱们马上研究研究......’
……田雨对发呆的王友清说:‘王书记,马上召开一个紧急的区委会议你看好不好?’
王友清点头说:‘好,好,大家研究,大家决定,大家负责任。……’
高大泉说:‘我在矿场上还遭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得马上跟区委汇报呐。’
王友清又连连点头,说:‘好吧,好吧,让大家都听听。真叫险呀!’”
这个段落,细致入微地描写出王友清从志得意满,到不愿相信、大惊失色、怒气冲冲、心有余悸、暗自庆幸的神情和心理变化过程,深刻表现了他虽具备基本的是非观、但更主要的是看重个人荣誉、遇到没有把握的紧急事就先考虑对自己的利害、怕担责任的思想意识。
随着故事发展,王友清对谷新民和高大泉的潜在态度逐渐发生改变。对于谷新民,当天门镇遭到暴雨围困粮食殆尽、谷新民又习惯性地想要求助囤积居奇的粮店资本家“售粮救急” 时,王友清突然地“第一次对身边这位领导者县长谷新民此时此地的这个做法产生了怀疑”,而当区长田雨提出动员农业社和互助组的农民运粮支援后,王友清“脸上的愁云渐渐消散了”、感到“一身轻松” ,以至当着谷新民的面脱口说出求助粮店资本家的办法“根本行不通”这样的批评之语。此后,王友清内心里“对老上级谷新民再不像过去那么迷信了”,“执行着谷新民的指示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地琢磨”。
而对于高大泉,王友清从认为他是“不得手、不顺心的干部”,到因为芳草地村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在全省出了名,在上级挂了号”而“初步感到”他是能让“区委领导推动起工作来……省心、省力、把握性大”的村干部,慢慢发展到“对高大泉的印象好了,或者说有点感情了”,直至“把高大泉看成自己的得力助手,有时候甚至把高大泉当成自己的主心骨,凡是芳草地做出来的事情他都觉得正确,凡是芳草地提出的要求他都尽力满足,凡是芳草地开展一件新的工作他都支持,有时候觉得没有把握、拿不准主意他也不反对,甚至在多数情况下他根本不加以怀疑,因为以往几年的宗宗件件的事情证明,高大泉带领芳草地迈的哪一个步子都是对的。作为一个区委书记,……芳草地的每一个创举都会在天门区的成绩表上增加一分,这不是他区委书记的荣誉吗?”他总是习惯性地把个人利害与做好工作掺杂在一起。
因为上述种种,当谷新民想借着上面刮来的“压缩合作社”风潮压服高大泉、鼓动芳草地的农民“退社”时,王友清虽然“不敢劝阻这位县长”,内心却希望“芳草地农业社完整无缺”,他不“顺着”谷新民“准备好的框子”,尽力用冷静谨慎的话语给谷新民泄火,暗中“帮着”高大泉。
小说作者以细腻的描写表现王友清微妙的思想、言行变化,塑造出一个复杂的“区委书记”形象。
王友清是解放初期一类人的典型,他们身为革命干部在思想上是“糊里糊涂”的,在正确的领导下他们能干好事,在错误的引导下他们也办坏事。小说作者把王友清判定为“被革命洪流卷进大时代海洋里”的人,极为透彻。
小说中还塑造了谷新民、张金发、刘维等另类“被革命洪流卷进大时代海洋里”的人物。
作者给县长谷新民的设定是:“大仓镇的谷家大财主”的儿子,当过教师,全国抗战爆发后出于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参加街头政治运动,随后加入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曾经被捕遭受严刑拷打但没有叛变。土地改革结束后,他推崇上面某些人的“发家竞赛”指示,宣称“农民自然有高度的生产积极性,用不着我们给他们划道道,撒开手让他们发家,设法把他们闹发家的热情调动起来,就会为我们将来搞社会主义创造出条件、打下基础”,向王友清等部下暧昧地灌输暗中抵制县委推进互助合作化决议的论调,说是“不争论,秋后算账再论输赢”。他平时“是一副有修养的老干部的姿态”,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经调查研究,只凭下级汇报、按照自己坚持的“发家竞赛”的框子做决定。他自认为“同情农民”,常把“人道主义”挂在口中,但在实际言行中常常只对符合自己既定思想框子的人表示同情、实行“人道主义”。他“不同意”县委书记梁海山的“许多观点”,但“尊敬”梁海山的革命者品格,当梁海山因为发展农村合作化改革而被地委某些领导“扣在那里做反省检查”时,他“难以忍心抛开梁海山,而不跟自己的同志分担责任”。他面对作为农民、下级、经常做不符合自己“发家竞赛”思想的事儿的高大泉,则常常是“冷冷地”、“板着面孔”、“拉着长声质问”。县委按照上级指示作出增加棉花种植的决议,他因为不合自己的心意而在布置种棉工作会议上敷衍冷淡,省委某些领导发下“压缩合作社”的要求,他则因为符合自己的心意而大力传达、积极实行。他在农村“访问和巡视”时路过筑堤工地,曾“伸手夺过扁担,挑起土筐朝河堤上跑去”,并要求装土的人“多铲点,装满吧”……“老干部”谷新民的形象很是立体多面。
小说中对谷新民“两上聚仙楼”描写,把他的多面性展示得惟妙惟肖。
谷新民“一上聚仙楼”饭馆,是参加一个“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他“大大方方地坐在正当中一张放着厚厚软垫子的太师椅上”,“一边细嚼慢咽地吃着喝着,一边似用心又似乎不太注意地听着人们对政府感恩戴德的颂扬。他时而含笑不语,时而微微点头。当某个人谈到了关键问题,他就发表几句简短明确的意见,尽管听话的人表示惊叹不已,他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神态。这神态迫使在座的人增加对他的敬畏,有什么不满的话只能在心里边翻腾,不敢放肆无礼。”最后,他“看看一张张冲着他谦恭嘻笑的脸,点上一支烟,抽了几口,一字一板地说:‘各位所表示的爱国之情,都是可嘉的。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一个强大的祖国,政府欢迎和鼓励一切积极的行动。大家都应当遵照共同纲领的原则,本着爱国的精神,公私两利的政策,对国家对人民努力作出贡献,这是我最殷切的希望。……’” 作者以白描手法,活现了一位自信、和蔼又威严的“老革命”、“大”县长。
“二上聚仙楼”,是天门镇遭受暴雨围困、粮食短缺,奸商们囤积粮食不卖,企图推高粮价谋取暴利,谷新民出于“对私人工商业一定要利用改造,只改造而不利用,则是对党的政策片面理解”的想法,“亲自冒雨召集商人们来座谈,号召他们来售粮应急”。奸商们故意迟迟不露面,聚在一起密谋要“等他县长跪下哀求,粮价提到我们要多少他就答应多少的时候”才售粮。谷新民只能“坐在那只没法靠一靠的凳子上,抽着自备的烟”耐心等待,他“身子习惯地朝后一靠,……一下子靠空,差一点闹个倒仰而栽到地下。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屁股下边坐着的不是他在县政府机关坐的那种藤椅,也不是在区公所坐的那种木椅,更不是去年的此时此地坐过的那一把有软垫子的太师椅,而是一个四方方、硬邦邦的凳子”,连一杯热茶都要区委书记王友清“亲自张罗要求”才得到。被奸商们冷遇和嘲骂的谷新民,“从心底产生一股受辱的气恼”,极力“把自己那冲动的感情控制住”,丢下“你告诉他们,政权是共产党的,他们如果非法胡为,将是自找苦吃”的话退场而去。这时的谷新民“脸色苍白,二目无神”,成了一个受了欺负的无助的可怜人。
品性多面的“老干部”谷新民虽然当初看起来是主动投入“革命洪流”,其实并没有在思想上真正加入共产党,本质上仍然是“被革命洪流卷进大时代海洋里”的人。小说里的谷新民“整治”高大泉和芳草地农业社的图谋失败了,但他的思想恐怕难以纠正——当年有不少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而从二十年后推行农村“分田单干”的那些人身上,也可以看到他的影子。
芳草地村长张金发出身贫苦农家,但在地主歪嘴子家做工时就巴结地主,曾为地主在麦收季节施鬼计盘剥“打短工”农民而卖力。土改中他抓住机会带头斗争歪嘴子,积极查找歪嘴子隐藏的家财,赢得某些土改工作组干部的重视,入了党,当了村长,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宣传动员,以至一度“喊哑了嗓子”。土改后,“发家竞赛”的上级文件使他贪财谋利的秉性复活,他梦想着利用村长的威信、权力,通过剥削村民率先发家致富,为此反对、怠慢以至阻挠破坏村里的互助合作事业,受到党组织批评处分后不思悔改,变本加厉,伙同漏网富农冯少怀和粮店奸商沈义仁倒卖粮食、出卖政府经济情报、破坏统购统销,逐渐“从不自觉地反党,变成自觉地反党”,最终被清除出党。
作者以许多生动故事表现张金发逐渐堕落的过程,其中高大泉组织动员村民支援被洪水围困的天门镇前后发生的故事就很典型。
第三部四十六章,村长张金发丢下麦收工作,与冯少怀一起到天门镇粮食市场上炒买炒卖粮食,村党支部书记高大泉知道后,找张金发做思想工作:
“高大泉……从粮食问题跟张金发谈起,他说:‘如今的粮食问题,关系着党的大局,关系着国家的大事。我们一个党员,一个穷苦出身的庄稼人,得为国家想,为群众想,可不能把爱国思想扔到一边,趁机捞便宜,揩老百姓的油肥自己呀!’
张金发使劲儿抽了几口烟,做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心里想: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想再断我的路,不用费心,办不到了!
高大泉能耐着性子做工作,可是不能多磨时间,他还有好多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办理。于是,他开始追问张金发:‘你们今天到集上去,是不是又鼓捣粮食了?’
张金发不惊不愣,也不迟疑,因为早有准备。他故意气恼地回答:‘刚才我不是告诉你了,我去说媒吗?’
高大泉不信他的谎话,继续追问:‘如果说你这回真没抓粮食的话,你们是不是试探着步子,想要动手搞呢?’
张金发把烟根扔到地下,用脚踩着,说:‘你别总是这么前追后拿的不放心好不好?不管有啥新精神,反正我一不去偷,二不去盗,不出圈,不过线,能怎么着我呢?’
高大泉说:‘这几年你的心思不正,脚步偏,净做出圈、过线事儿嘛!我不光对你不放心,还实在让人替你提着心呐!’
张金发不以为然地摇摇脑袋:‘你老是疑神疑鬼的,我有啥办法呢?’
高大泉激动地站起身,朝张金发跟前迈一步,问他:‘还记得咱们成立党支部那会儿,田雨同志对你说的那句话吗?’
张金发一翻白眼:‘什么话?’
高大泉轻轻地哼了一声,说:‘我知道你忘了,当时你就没有用心听!……田雨同志当时对你说,他最担心的是,你从不自觉地反党,变成自觉地反党......’
张金发一听这话就急眼了,跳着脚喊:‘谁反党了?你今个得给我说清楚、道明白!’
高大泉毫不回避地说:‘你一连串的行为,已经有了这样的危险!’
‘那你就处分我好了!’
‘我不乐意有那一天。我想挽救你......’
‘只要你们不生着法儿害我,就没那一天!’
高大泉……说:‘……你说假话,办坏事,走邪路,还这样理直气壮!…… 你必须马上给我说清楚,你今儿个到天门镇到底干了什么勾当?’
张金发哼了一声:‘说清楚也没啥了不起。我们设法给社员谋点福利,有啥错处?犯了啥罪?’
高大泉质问他:‘用害国家坑人民的办法,谋个人的福利,这是哪个阶级的手段呢?’
张金发使劲儿顶:‘买卖自由,名正言顺,两厢情愿,谁坑害谁啦?’……”
这一段,张金发对自己倒卖粮食的行为,从说谎抵赖,到“理直气壮”地承认,写出了对抗心理的升级。而不久后,高大泉接到区委通知组织粮食支援天门镇,张金发则偷偷装运一车粮食先赶到镇上沈记粮店,把大批粮食即将运到的消息泄露给囤积粮食不卖的奸商沈义仁,共同谋划赶紧高价大量售粮,大赚一笔,却被高大泉抓了个现行:
“张金发一边慌乱地往后大门跑,一边往雨衣的袖子里伸胳膊,还不住地扭回头来张望。
……张金发抬腿往外迈。一个人,像一根石头柱子立在他的面前。张金发吸了一口冷气,不由倒退一步。
高大泉愤怒地盯着他,低声而有力地质问他:‘张金发,你还想溜过去吗?’
张金发脸色煞白:‘我.....’
‘你可耻!’
‘我来这儿找口水喝……’
‘你是来入伙喝人民的血!’
张金发故意瞪眼珠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高大泉一伸手,指着棚里正吃料的大黑骡子:‘你睁开眼看看,人证物证俱在,赖不掉的!’
……高大泉……用手一指,命令张金发:‘走,到区委会去!’
张金发只好乖乖地走了。
……高大泉像押俘虏似的把张金发带到了区公所里。”
这一段的描写,使张金发做贼心虚的神态、心理展现无遗。
张金发这个人物,在“被革命洪流卷进大时代海洋里”时有着明确的投机意识。在中国革命中,这样的投机分子也不鲜见的。
县长谷新民的警卫员刘维,则是另一类投机分子。他是谷新民“一个旧时同学的孩子”,解放后靠“同窗之谊”被谷新民招到身边。这孩子“头脑聪明,口齿伶俐,办事利落”,最初很受大家喜欢,但时间一长,受谷新民熏染,渐渐变得轻浮起来,爱虚荣,爱传小道消息,常打着“县领导”旗号办事,按干部职务不同以不同的态度区别对待。他一切都以谷新民的意志为行事准则,对谷新民有着人身依附意识,实际上可以说是谷新民的“亲兵”。谷新民宠爱他,护着他,把他提拔成梨花渡乡党总支书记。他工作不负责,时常挖空心思想找一个漂亮的知识分子女干部当老婆,但给谷新民“汇报情况”却很勤快。小说中对他的着墨也不算多,但仍然刻画得入木三分。
小说中写到:高大泉因为发现东方红农业社发展壮大后出现了一些问题,写信向县委反映,但很久没有听到回音,就到乡政府去询问,正好碰见一位孤寡老人因为农业社逼他退社来乡里求助,只见:
“身上披着有狐皮领大衣、穿着新做的蓝斜纹布棉制服的刘维, ……见那个老头冲着他要开口,就抢先皱起眉头对老头说:‘你怎么又来了?’
老头被堵了这么一句,也不计较,仍是一副温顺的神态,说:‘刘书记,我的事儿没办妥当,我还得来麻烦你。’
刘维依然冷冷地说:‘不是跟你讲过多少遍了吗?还怎么办妥当?’
‘同志,那样办,我们这一老一小,活不下去呀!……’
‘找找亲戚朋友嘛!’
‘十天半个月的靠亲戚行,太长了,人家也是难办呐......’ ‘哦,亲戚难办,农业社就好办了?把人家集体给拖垮了,谁负责任?’
‘刘书记,我保证不连累农业社,你放心。眼下,我还能摸索着干点活儿,我这小孙子,过几年也就顶用了。’
‘那就先对付过,等孩子能劳动了再说。’
‘同志,同志……’
刘维不耐烦地一扭头,冲着高大泉微微一笑:‘高副乡长,过节好哇?我刚从县里回来,正想给你拜年去呐……’
高大泉……问:‘这老大爷是哪村的?’
刘维说:‘就这村的。’
‘他……’
‘唉,乡里这种麻烦事儿可多了,没法儿推开。你快到办公室里暖和暖和吧。’
……刘维推着高大泉说:‘这老头跟说书的学的,能聊着哪,快躲开他吧!’
老头激动地说:‘刘书记,你不用怕,我不会咬住他不放。……’他面向高大泉:‘你说说,他们还是共产党员,硬劝我头一批老社员退社,这对不对?’
刘维刚要阻拦,高大泉却毫不迟疑地开了口……
高大泉见老人的背影消失在一片枯树林子那边,才转过身来。刘维一边跟着他往屋走,一边埋怨说:‘大泉同志,你这杠插得可不怎么好。’……”
共产党的乡党总支书记刘维,对信任共产党、前来求助的孤寡老人冷若冰霜,毫无同情之心。其实,他对高大泉也是面上和内心两张皮:因为“高大泉不是谷新民县长称心如意的干部,刘维自然而然地也讨厌高大泉。来到梨花渡乡以后,一种不着边际、不成比例的嫉妒心理,使他对高大泉既有点敬畏,又有点憎恨”,他经常就高大泉的事儿向谷新民打小报告。
在“压缩合作社”风潮中,刘维跟着谷新民到芳草地村去“整治”高大泉,这时的他“是个最轻松的人。县委犯了多大的错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区里的工作以后再难开展,追究责任也难摸到他的脑袋上;在乡里,他刚到不久,也不担什么重担子。对高大泉本来就系着思想疙瘩,因为朱铁汉变成了他的情敌,那种无名的恨怨越发加重了,这回如果高大泉垮了台,朱铁汉肯定得跟着完蛋。……朱铁汉自然而然地就会让出位子,一个有地位又显有才干的乡总支书记,跟一个撸锄杠的农民、犯了错的村干部站在一块儿,可爱的教师陈爱农会挑选哪个?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这一次芳草地之行,对刘维的婚姻来说是成败的关健时刻。刘维有信心取得胜利。”怀着这种心理,刘维找着机会就跳出来攻击高大泉:
王友清提到高大泉病着,刘维却说:“他那是搞急躁冒进搞的。命也不顾,拄着棍子,到处串通了,逼着人们合并。”
王友清“小心地”建议“对高大泉,我认为不能伤害他……”,刘维立刻“不客气地驳斥他:‘他一定要跟上级的指示顶牛,也得保护他呀?我认为这是原则问题!’”
谷新民提到张金发的问题,王友清认为“不能让他翻案”,“刘维又驳斥他:‘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得实事求是嘛!’”
高大泉向谷新民解释芳草地村的“大联社”是按着发展生产的需要和社员要求办起来的,刘维立刻“忍不住地喊起来了:‘你快算了吧!你们这样干,遭到群众强烈反对!连你的老伙计,都受不了你命令主义,拉牛退了社,你敢说没有这事儿?’”
邓久宽当着谷新民的面要“退社”,要求“你们马上给我退地”,朱铁汉根据农业社规章告知邓久宽要补偿那块地已经投入的“工钱、肥料和籽种钱”后才能退,刘维就马上“帮腔了:‘这不是刁难人吗?’”
谷新民吓唬高大泉说省委、地委会派工作组来处理他拒绝“压缩”农业社的问题,高大泉说欢迎工作组来看看,刘维又“冲他喊:‘高大泉,你也太不像话了!你知道不知道,谷县长本来应当撤你的职,现在都千方百计保护你?’高大泉不急不火地说:‘我个人没啥。我只要求各级领导正确地贯彻上级的指示,真心实意地保护农民的社会主义的热情……’刘维一拍桌子吼道:‘我看你是冷心肝、狠心肠!谷县长对你这样的耐心,这样的宽大,你就寸步不让?’”
农业社饲养场起火后,谷新民想诱使、逼迫邓久宽承认纵火,高大泉指出纵火者不会是邓久宽,刘维就“代替谷新民杀了出来:‘我也请问一声支书同志,这火不是邓久宽放的,你说是谁放的?’王友清也倾向高大泉的看法了,就想打个圆场,对刘维说:‘咱们再进一步调查调查,反正谁放了火,跑不了他...... ’刘维说:‘这不能含糊!他要给邓久宽开脱,就得交出放火的人!’”
……
小说通过刘维时不时蛮不讲理、大喊大叫攻击高大泉的神态和言语,表现了他极力在谷新民面前表“忠心”、极力要攻倒高大泉以泄憎恨的嚣张和愚蠢。
这几个“被革命洪流卷进大时代海洋里”的人物,是新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具有巨大的文学价值;同时,对人们理解新中国发展斗争的复杂坎坷也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网友评论
共有0条评论(查看)